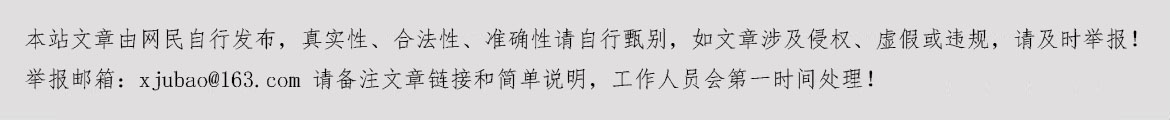导演:徐童
编剧:徐童
主演:苗苗
类型: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
上映时间:2008
片长:99分钟
文:何聊生|主播:上官文露
/Part01
「它讲述不一样的“性工作者”」
有这样一个女性群体,她们有很多“名字”,“站街女”、“小姐”、“妓女”、“鸡”、“援交妹”、“应召女郎”……而这种种或侮辱性或委婉的称呼,都可以囊括进一个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词——性工作者。
国内将镜头对准性工作者的影视作品有很多,《金陵十三钗》是妓女的“义书”,金陵河畔风情万种的玉墨摇身一变成为了唱诗班的女学生,为这个群体在世俗眼光中的“脏污”渡上一层纯净,但这种升华仍然持有一副有色的眼镜,它在另一意义上显出了人们对于妓女的偏见与无情的眼光。
《金鸡》《金鸡2》《金鸡SSS》是妓女的“笑忘书”,以一种解构严肃的戏谑姿态讲述妓女的人生,讲小人物的爱恨挣扎,以表达自嘲与不屈的香江精神。《胭脂扣》是妓女的情书,最不能忘是梅姑鼻下那颗如墨的情痣,相约殉情却独活的十二少年老时一泡苟且的尿液,将当年那定情之句冲散得凉薄。
《喜剧之王》取景地石澳的海滩上放置着的是妓女的“卑微之书”,尹天仇的那句“我养你啊”和海风一起吹得女孩的心底柔软却又战栗起来,身为舞女,柳飘飘不敢爱也不敢恨。
但《麦收》与如上所述的这些作品都不同,它剔除了人为的戏剧化的处理,真实得过于粗糙,而奇异的是,这种真实不会带来人们对于所思问题的明晰,相反地,它将给人带来一种稍显陌生的困惑。
《麦收》是纪录片导演徐童的“游民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此前我讲述过“游民三部曲”的另外一部《算命》),它所纪录的是性工作者真正的生活,尊严与爱情。不,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纪录的仅仅只是人真正的生活,尊严与爱情。
/Part02
「“妓女”与尊严」
苗苗是河北人,20岁左右的她在北京的一间小发廊做“小姐”。苗苗的生活圈子里包括了和她一样的“小姐”和前来买春的客人——外来妹与打工汉。
她来自底层,也出卖给底层,消费与被消费者共同生活在城市边缘逼仄的空间里。
在《麦收》的镜头下,苗苗穿着廉价且暴露的衣服穿梭在北京郊区的大街小巷之间,无论如何浓妆艳抹都称不上是漂亮。这副景象也许会击碎文人在文学作品里努力营造的有关“妓女”的一切泡影——贫苦的出身与不合时宜的美貌,但苗苗只有前者。
片子一开头,就是苗苗和其他同事在工作地点“炮房”议论客人有多坏,一个抱怨客人整个晚上都在折腾她,一个劲儿的乱摸,让她通宵没睡,另一个又抱怨客人让她多做了几次。
两个姐妹说了半天,唯独苗苗没开口抱怨,这或许可以被视作是一种职业性,所谓职业性,就是明白收获与代价的对等,这种职业性让她闭上了嘴。
如果说,此刻的苗苗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得已的隐忍和立场的模糊感,那么随着《麦收》的叙述的展开,我们将发现,苗苗的底线是极其清晰的。
那是有一次,苗苗跟两个朋友喝酒,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句“让她歇x。”(侮辱性语言)
苗苗变了脸色。你说啥?你再把那话重复一遍。
对方看不好下台,只一个劲儿的贬低自己说自己蠢,没文化。农村出来的啥也不懂。
苗苗反问一句“我有文化吗?”
直到一旁打圆场的男人说“要想别人尊重你,你首先得尊重别人。”苗苗接了一句“这就是生存之道”,掷地有声。
苗苗的脸上是几乎永远挂着笑的,和姐妹们相互调戏,开开带黄腔的玩笑不算什么,但精神上的受辱始终是人的逆鳞,哪怕在他人眼中,她的职业是卑贱的、无尊严可言的。
也许,性工作者出卖肉体在常人眼中可能就等于出卖尊严,而出卖尊严就被认为等于可以被亵玩和戏说。但是《麦收》回答了一切,那些在“炮房”中大肆谈论接客细节丝毫不感到羞赧的女人们,也会说出“我不要睡的呀,你以为你出了几毛钱有啥了不起啊”这样的话。这代表着一种呐喊,喊出她们不是完全被动的、甚至在精神上也任人宰割的群体。
一次100,包夜300。身体被贱卖了,但尊严作为人的重要尺度,始终是不容售卖的。
/Part03
「没有眼光就是一种有情的眼光」
很多人对性工作者的生活的窥探欲本质上就是一种猎奇,他们有自己预设的想看的内容,这内容无非就是,她们到底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她们是不是行尸走肉一般过着没有尊严、没有灵魂的生活?而《麦收》会让猎奇者失望,因为你会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苗苗和从事一般职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她同样有自己的工作以继生存,需要为家庭支出,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也有自己的闲余消遣。这是徐童在“游民三部曲”中表达的一种的可贵立场。不是呼吁尊重和关切,而是不持有异样的眼光。
纪录片导演周浩认为,纪录片要呈现生活的混沌和不确定性,意为生活中的一切并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
《麦收》或许平淡、粗糙,但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里,性工作者不再是传统视野下的,一种应当被看轻的职业。它将引起曾持有轻视立场的观众的疑惑,心理上的混沌和不确定。
因为,也许原本你看到的是她们在大城市的边缘多么难以立足,而事实上她们在自己那片巴掌大的出租房、发廊里划定了自己的国度,除了接客她们也会敞开了玩,一天不营业,在发廊里随着电子舞曲自娱自乐地起舞。
你也可以看到她们如何消遣、找乐子,她们会花上100块钱到KTV找男性性工作者陪伴。在那里没人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她们可以在陌生的环境暂时摆脱性工作者的身份。
而这个背后其实透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它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她们在工作之外,有自己另外的需要释放的真实欲望。
也许你认为她们在工作引起的创伤中已经丧失了爱的向往与能力,想象不到她们能拥有正常的感情生活,但事实上爱情中的她们像所有沐浴爱河的人一般鲜活。
你甚至可以看到她们防御之姿背后柔软的贝肉,苗苗最好的朋友格格,个性鲜明,客人打来电话,她可以脏话连篇地将对方喝退,但却在男友面前温驯有如绵羊,甚至没有大声说过话。
在分手之后,她也会在接前男友电话之前犹犹豫豫,直至错过了一通又一通电话,甚至为了不撞见前男友,连走路都要注意躲着。
《麦收》没有讲述格格这种犹豫背后的原因,但却透露出被“妓女”这一身份遮蔽了的身为女性真正的爱与欲——对于爱与被爱,她是那么小心翼翼。
苗苗的恋情经历也很平常,有被追求、有甜蜜、有背叛。苗苗这样讲述她与男友许金强的经历:
“我跟他是在那个高西店,就我上班的那地儿认识的,总共也就见过两次嘛。然后之后就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就天天啊,没事儿他能达到三四五个电话。”
“你就想吧,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特新鲜,有事没事就打个电话,宝宝在干嘛?然后,就是,就说来说去也就那两句话。”
但最终苗苗接到一通电话,男友在电话中长篇大论最终只为了通报一个结局——分手。许金强移情别恋,搭上了苗苗的好友格格。
恋爱、腻歪、分手,这些环节往往都是如出一辙,但在分手这一环节,苗苗甚至显示出了一般女性难以拥有的气度,她在镜头前说,绝不会因为男人与姐们闹掰。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出于她对格格与她同命运的一种惺惺相惜,以及在这种职业生存环境下对于友情的格外珍视。
《麦收》是徐童“游民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令很多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徐童的出身背景,徐童生于一个导演家庭,父亲是获奖多次的知名导演,而徐童本人的成长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80年代那种艺术家理想的影响。于是人们会怀疑,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偏偏愿意将镜头对准“草芥”式的人物?
徐童认为自己实际上和这些人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困境,他曾为了拍纪录片卖掉房子背水一战。我们不去评价徐童的困境与他镜头下的人的困境是否可以拿来作比,但可以确定的是,徐童至少是在努力摆脱知识分子立场的局限性,也正是这种跳脱让他选择将镜头对准这些群体。纪录,是为了被看见。而改变的第一步,则是被看见。
最后,还是想再次提及纪录片《算命》中所表达的能驳回一切同情与鄙夷眼光的那段话——“这话说的,人那没乐趣呀,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太,太这个,无情了。”
或许,真正有情的眼光,便是没有眼光。
【本期话题】:你如何看待性工作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文作者简介
何聊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为人不得不痛,不写不快。
上官文露读书会签约作家,曾发表多篇书评、影评。
原创小说作品:短篇小说《甲醛男女》《世界这么大,跟你有鸡毛关系》等。
本文主播简介
上官文露,文学博士,曾任北京电视台新闻记者、主持人。创办文学名著解读网络电台《上官文露读书会》,点击量逾17亿人次。著有中篇小说《时代曲》《人生欢》,短篇小说《赌徒》《锈鹃》《婴》《永生花》《结婚大师》等,电影短片剧本《加油吧!勃拉姆斯》《美错》等。
音频制作:上官文露声音工作室—昊泽
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
本期插图
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