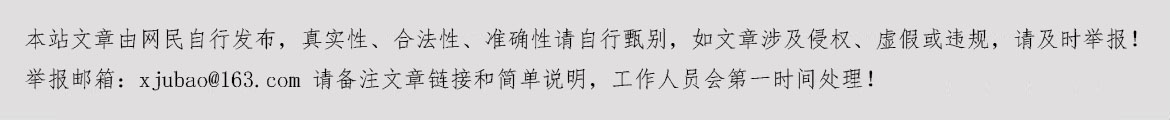在物质保障、鼓励举措没有跟进时,谈全面放开生育,没有任何意义
文 | 赵天宇 辛颖
图/unsplash
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陈柏,结婚已有几年,30岁还没生孩子。虽然没生,但做不到无视。相反,每隔一段时间,他和同在民企供职的妻子就免不了聊到这件事——年龄、住房、工作、父母,家庭生活的每个切面其实都在隐隐提醒着他们。
2021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微信推送的一篇工作论文,似乎是对陈柏境况的高度版概括,“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
陈柏瞄到这则消息,觉得自己就是需要“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的目标人群。央行这篇文章非常抢眼,阅读量迅速10万+。
该文建议,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然而,陈柏说,这些外界讨论和口头鼓励,完全无法说服一个家庭做出“生孩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认同大中城市里青年人面临的生育压力。这里吸引了大量的青壮年,是新生人口的主力,但人口集聚导致购房压力大、教育资源紧张。
同时,“现在是非常迫切的要鼓励人们生育,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有一部分想生的人就会错过生育期,到时候就不能生了。”王智勇告诉《财经》记者。
经济成本决定生不生
“我担心生活质量下降,一去不复返”,面对生育的选择,这是陈柏和妻子的第一想法。
在北上广,有一大群陈柏们。对他们来说,生孩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脚跨到了河对岸,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无法回头。
生育成本太高了。
他和妻子年龄相仿,都不是北京本地人,双方父母支持在北京五环外买了套房,已经比很多人幸运。然而,五环外,没有太好的学校。
一旦有孩子,大多数人得考虑租住或者买靠近学区的房子。在北京的学区房,划片中关村三小的蜂鸟家园小区,4月16日在链家网上每平米的价格超过17万元,50多平米的一室,房价轻松突破900万元。若在这个小区租一套50平米左右的小型公寓,每个月至少要7000元。
900万元,已经超过很多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润了。比如顺灏股份,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783万元,而这家公司已经经营了17年。
陈柏的日常工作很忙,晚上九点以后才到家是常事,每个月还要出差几次。回到家里他只想放松生活,夫妻二人不愿意耗尽精力在日复一日的育儿中。
陈柏家每个月除去还贷款,收入足够生活,然而一旦生育,势必打破平衡。于是他们一起卡在生育未知数的尴尬几年里。
这些一线城市的育龄人口,想法和困境是共通的。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在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分析了上海地区人口生育决策的决定因素。结果并不意外:包括市卫健委、市教委、市医保局、妇幼保健机构、育龄女性在内的所有39名受访者,都提到了经济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包括住房、生活和养育成本。
研究者坦言,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难以忽视,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会对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上海受访的一孩和二孩母亲均提到,各类辅导班及兴趣班的支出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一位育龄的二孩母亲说:“辅导作业班、舞蹈班、课余兴趣班很多,1个孩子最少1个月光上课要花1000块钱。”
更多家庭里,一个月1000元的标准根本不够。北京一位一孩母亲告诉《财经》记者,孩子课外班每个月得花2000元,另外每周带出去消费一次,也得三五百元。她还没给孩子报网课,听说是越来越贵了。
女性在工作和生孩之间的抉择
不想生育,并不是陈柏一家的选择。新生儿真的越来越少了。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
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新生儿的户籍登记不及时,因此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的准确数据,要等待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将在今年4月公布。
截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出生人口数量已经不乐观。
中国出生人口近十年来的高峰出现在2016年,全年出生1786万人。此后,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逐年下滑,2019年下降到全年仅出生1465万人。
历数全年出生人口数量,2019年的1465万人,是自从1962年以来的最低值。1961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187万人,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数据来自Wind; 制表/《财经》实习生 王天琳
具体到各地,情况类似。例如上海市生育率,已被研究者认为是处于极低水平,即便自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为0.9(2018年)。
从数据可以看出,仅宏观政策层面的调整,在短时间内扭转低生育水平的效果不佳。
这次令陈柏们很有共鸣的央行工作论文里,同样直指人口数量问题: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数量从急剧膨胀到增长趋缓,人口结构从金字塔到长方形,而且中国的人口转型时间更短、老龄化更迅速、少子化更严重。
“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提出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东北的人口问题尤为凸显。以国企居多的东北,以往是计划生育的前沿阵地,这届90后的东北人,多数是独生子女。但现在却要掉头回去多生孩子,很多人没这个概念。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口已经持续出现负增长,转向正增长的难度非常大。如果在东北地区试点全面放开生育,对减缓人口下降趋势不能说没有效果,能够起到一定的全国示范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表示,中国正处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重要节点。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
在新生儿数量下滑的背后,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面临的困境不容忽视。
央行工作论文中提到,1950年-2019年,中国生育率下降快,因素包括育龄妇女减少、生育窗口期缩短,也带动生育率加速下降。
女性正面临着从生理到心理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职业女性。
生育不是一个短期事件,从怀孕、分娩再到哺乳,都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女性需要更多地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甚至会在职场遭遇“隐性歧视”,因此女性劳动参与率愈高,生育机会成本就愈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发现,有生育经历的3名受访者曾表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生育的影响。
“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她要平衡自己的事业发展、工作目标和人生目标,抵消生育意愿的因素在不断增加。”陆杰华告诉《财经》记者。
放开“三孩”,能解决问题吗?
“放开生育”,在学者们中早已达成共识,现在是呼吁“放开三孩”。
“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央行工作论文中写道。
携程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去年11月撰文写到,只放开三孩是不够的,而是要全面放开生育。并提出,要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维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想让犹豫中的陈柏一家下决心生孩子,就得考虑解决他们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
“人口学界几年前就达成共识,首先必须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没什么作用,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通过物质激励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王智勇说,不仅是生育放开,配套的措施跟上去才有可能有效果。
上海的研究人员指出,相较于其他低生育水平国家提供的多样性津贴福利,如生育奖金、育儿补助津贴等,中国尚缺乏长期且覆盖面广的鼓励生育福利政策。
王智勇建议,针对住房、教育问题,需要城市发展规划提前做好应对,刻不容缓。现在年轻人购房压力很大,想多生一个孩子就需要更大的房子,买不起怎么生呢?如果设置一些激励措施,比如给有二胎的家庭一些优惠来购买改善性住房,比如首付比例低一点、贷款率低一点等等,那顾虑就会少一些。
在陈柏身边,有多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工作的朋友,共同特点是来自北方小城,大学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到大城市工作。结婚的不少,拖到30岁上下的关口,竟然没有一个人生孩子。
“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小孩也是育龄人群的顾虑;如果多生几个,那老人也顾不过来。”王智勇说,难题在于商业化的托幼机构收费非常高,政府可否鼓励社区发展一些托幼机构来帮助,以及从小学开始的一系列教育保障。
比如北京,2020年小学入学人数在22万人左右,而学位缺口大约是8万人左右,小学上学都这么难,那么从一开始陈柏们就难下决心。
“我们能看到卫健委、民政部在这方面是有在推进的,但是还不够。”王智勇认为,在物质保障、鼓励举措没有跟进时,谈全面放开生育,没有任何意义。
(文中陈柏为化名)